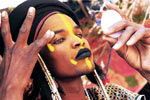初次见面是在凤凰卫视“寻找远去的家园”节目上,印象不深,只依稀记得那里的房子很老,那里的人很迷信,那里还有一位老道士。
与它的再遇是在无边际的互联网上,借助搜索引擎,显示屏上很快出现了比我想中要多的搜索结果,内容简单而雷同,夹杂着少许介绍,里面提到了著名记者张新民的《流坑——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最后标本》,一本图文双佳的书,还有,那里的人们基本上都姓董。
与它的邂逅是在一个旧书摊里,当时颇有一种“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喜悦。遍寻未果的《流坑》竟意外地出现眼前:大32开铜版纸精印,一百多页,几十幅黑白图片,一段段渐被人遗忘的故事……书价五折之后仍要46大元,但也在所不辞了。
于是,心中便有了期待,期待与它的直面。
2002年春节,选择了一个人独自前往,原因也不复杂,不外乎是有钱的朋友没时间,有时间的说没钱,两样都有的对却对这个闻所未闻的地方毫无兴趣。因为之前还去了婺源,所以到流坑的游程应该从上饶算起。从上饶到鹰潭,鹰潭到抚州,再到乐安,然后到流坑,为了节约时间,我选择了短距离城市间衔接的乘车方案,纵是如此,不到 400公里的路程足足跑了10个小时。记得曾经五下流坑的张新民说过“第一次到流坑,80公里的路跑了一天”,与之相比,我已感万幸。进了流坑,一个中年汉子把我叫住,问是否需要住宿,于是跟他进了风味餐馆,听他介绍,原来就是《流坑》书中提到的董家兴,热情、老实,略带少许生意人的精灵。屋子虽简陋,却也曾是凤凰卫视、张新民、专家、学者、记者、学生、政府高官等驻足之处,当然,还有准备入住的我。卸下大包,提着尼康,拿着主人家提供的旅游图,我信步踱进了村子。
是的,流坑只是一条村子,但却是一条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村子,无论是状元楼上朱熹的墨迹、存仁堂内精美的壁画、文馆内屋顶上华丽的藻井、麒麟厅前的照壁抑或“理学名家”门前的石狮,无不记录着它曾经的辉煌。村子很大,巷子按一纵七横布局,两旁房子鳞次栉比,朴实素雅,均为青砖灰瓦。屋内堂上有匾,门旁有联,雕刻也相当精美,确为徐霞客说的“万家之市”。村子里很热闹,男人在打麻将或闲聊,女人们在张罗着晚饭,小孩子们无忧地嬉戏,老人们则漠然地打发着时光。我举起相机对准他们,却发现他们没有一丝异样,可能近年来到此拍摄旅游和研究的人太多了,麻木了,只有几个小孩还兴致勃勃追着要我给他们拍照。不知不觉在村子里转了一个多小时,见到了《流坑》书中提到的大宾第、丁字路口的理发店、位于中巷的中药铺、墙上文革时期的图画、颓败的庙宇等等。的确,流坑已今非昔比了,给人的感觉第一是破,第二是脏。卵石铺的路面不知道已有多少年了,非常突尤,随便一所房子都可能有几百年,岁月就这样在断墙残瓦中不经意地流逝,千年弹指一挥间,怎教人不感叹韶华飞逝,难以复再?!
吃过晚饭,听说村里今晚有“何杨灯会”——一个存在了八、九百年的习俗,每年正月初九都会举行。黄昏时分,几名老者敲锣打鼓,并以火把引路,一名当年结婚的青年男子手捧约40公分高的何杨神菩萨像紧跟其后。队伍会走遍全村各家各户,为村民祈福。而村中家家都会摆设香案,燃放鞭炮迎接,仪式会通宵进行。果然,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彻夜未停。据说,初十流坑还有更大规模的“游菩萨”仪式,正月里也有富有地方特色的“傩舞”,可惜,在短暂逗留的不到一天时间里未能一见,至于流坑的道士更无暇细寻。
第二天起来,再次走进村子,感觉上更热闹了,扛着农具出工的人们,河边洗衣的妇女,市集上买卖东西的村民,蹲在门口刷牙的小孩子,静静流淌着的生活气息让人觉得它不是或不应该是一个旅游区。事实上,到流坑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看它的古迹,而是看这里人们的生活。在状元楼前,我遇到了正在玩耍的董福昆,流坑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他要我帮他拍照,我顺便也让他带路,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他领着我在巷子里穿堂入室,当然,我也帮他留下了 “倩影”。小家伙很机灵,还帮我拍了两张。董福昆告诉我,他家六口人,四个在外面打工,分别是父母、19岁的哥哥和18岁的姐姐,他与另一个15岁的姐姐由叔叔家照顾。这其实反映了流坑家庭普遍存在的情况,一是违反国家计生政策,二是年青人到外面打工的多。
又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了,崭新的水泥路渐渐拉远了我与流坑的距离,而思绪却一度失落在那个满目苍夷的标本里。与西藏青海的壮美、故宫长城的恢宏、苏州园林的雅致、黄河壶口的磅礴相比,流坑也许微不足道,但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坚韧性和由宗法制度所巩固强化的血缘关系,以及儒家理学的传统思想,使它历经战乱却只损皮毛,遗世独立,实在不得不令人惊叹。历史沉淀千年而变得厚重,让人忆古伤今,百感交集。它原计原味却不张扬炫耀,虽不浪漫婉约却也质朴风淳,纵已怆然却也是英雄迟暮。
近年来,旅游开发和村民外出打工,使很多新的思想和观念随之而至。古屋前站着的时髦女郎、集市里新装的IC卡电话、小店里出售的可口可乐,与外面世界距离的缩少似乎已指日可待,新与旧的撞击也只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役。一片破墟烂房,一堆陈风旧俗,几个顽固老头,在挟经济利益加速器的时间巨轮下,将被辗糅得粉身碎骨。状元楼前扫地的老头都会让我花15块钱请他带路了,民风的淳朴也许只是传说中的故事。假以时日,象“何杨灯会”这些仪式都会变成仅供游客们观看的表演了。人们也许永远也搞不清楚旅游开发对于这个标本是救治的良方抑或扼杀的尖刀。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流坑的人们世代生活在这些风雨飘摇的老房子里,过着和祖先们一样的生活,供我们现代的人们参观。很矛盾是不是?所以,唯一可做的也许只能举起相机,将眼前的一切凝固。尽量拍吧,不用计较什么光线、角度、构图,只要把他们的生活拍下来,多拍一些,更多一些......
以后,这里的道路不再难行,房子不再残破,宾馆也将林立,戴着统一帽子的人们在各色小旗的指挥下纷沓而至,而一位名叫流坑的历史老人也将寿终正寝。
相关新闻
- 江西抚州特色美食介绍:抚州炒麦鸡2010-02-06 23:48:56
- 江西抚州特色美食介绍:崇仁麻鸡2010-02-06 23:46:20
- 江西抚州特色美食介绍:茶树菇2010-02-06 23:42:53
- 江西抚州特色美食介绍:石鱼2010-02-06 23:40:59
- 江西抚州特色美食介绍:抚州米线粉2010-02-06 23:38:18
- 江西宜春景点介绍:明月山风景区2010-02-06 23:23:19
- 江西宜春景点介绍:三爪仑2010-02-06 23:14:19
- 江西宜春景点介绍:竹山洞风景旅游区2010-02-06 23:04:29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
我有话说
流坑
流坑村位于江西省抚州地区乐安县西南部,总面积3.61平方公里,全村820户,4290人,大都为董姓家族。该村始建于五代南唐升元年间(937—942年),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有宋以来,全村文武状元各1名,进士33名,举人78人..
您还可以看看
热门新闻排行榜
| 闂傚倷绀侀幖顐﹀箠閹版澘纾块柕鍫濇閸欏繘鏌ㄩ悤鍌涘闂佽崵濮风亸銊╁箯閿燂拷闂備浇宕垫慨宥夊礃椤垳绱撴俊鐐€栧Λ鎴﹀箯閿燂拷 |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鎲搁柍缁樻閺岀喖骞嗚閺嗛亶姊婚崪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