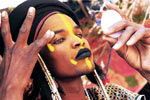早知如此
天太热,就没去参观世博会。影院里在放贾樟柯导演的《海上传奇》,听说与世博会有点关系,于是去捧场。电影的开头,陈丹青坐在一栋待拆迁的房子里讲古,表情严肃;结尾处,韩寒从赛车场的一头跑来,对着镜头调侃:将来有一天我拿到自己中意的总冠军后,我一定会很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其实我是一个作家。电影取了个意味深长的英文名字:I Wish I Knew,大概可以译成:早知如此。
以陈丹青和韩寒为坐标观察上海无疑是恰当的。若以二位为参照物观察文学,其实也同样能有所得。1970年,当17岁的陈丹青离开上海下乡插队时,文学对于他那代人而言曾经何等神圣——在赣南的山沟,以及全中国的山沟里,文学,尤其是苏联/俄罗斯文学,几乎就是知青们所能掌握的全部的外部世界。而整整四十年后,当28岁的韩寒终于办成了自己的文学刊物时,文学已经快要被人忘记。他在卷首语里自我激励说,虽然文学青年们已随花落去,但“我们总是要怀有理想的”。但毕竟令人遗憾的是,那曾经神圣无比的文学理想,如今只能“XX呵呵地矗立在那里”。
我并不想在此顺势感叹人心不古。其实更耐人寻味的是接下来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怀有理想?以及,文学为什么可以作为一种理想。
最近网上流传许多西方名校的“开放课程”视频。我凑巧看了两集,其中学到两句话,似乎可以部分地回答上面的问题。其中一课是古典音乐欣赏入门,教授说到,聆听古典音乐,可以令人窥见一个“更为美好”的、理想化的世界。我想,文学自然也有类似的功用。问题在于,有这种功能的事物不一而足,而当你所处的现实变动剧烈,同时不那么美好的时候,“更为美好”的事物就变得空前繁多,于是理想就会贬值为功利。这当然不能怪那些“没理想”的人。
另一课是古希腊文明史。为什么要学古希腊?因为古希腊很重要,教授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人自身的理性为基准建立规则而产生的文明。西方人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成就,无论科技还是文艺,都由希腊人奠基。而希腊人所奠之基,他反复强调,便是“理性”二字。这话我深能同意,其实,当年我们说的“德先生”,“赛先生”,都是理想,而我们从来不提理性,“理先生”。
所以我们的理想,从来也都没能实现,也就只好“总是怀有理想”。
相关新闻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
我有话说
您还可以看看
热门新闻排行榜
| 閺呯儤濮�璺�鐠у嫯顔� | 鐞涘奔绗熸稉鎾冲隘 |
|